宰信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最新诗集《深深地》
阿特伍德和最新出版的诗集
2020年年终,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最新诗集《深深地》(Dearly)出版,随后登顶各大年终书单,其中包括goodreads2020年度书选。这是阿特伍德十多年来第一本诗集。同题的诗歌表明了阿特伍德的主题:爱和哀恸,“深爱的人,相聚在这里/在这关闭的抽屉里,/正在褪色中,我想念你/我想念那消失了的,那早先离去了的。/我甚至想念仍在这里的。/我深深地想念你们。/我深深地为你们哀恸。”
阿特伍德发表了诗歌自述,发表于《卫报》,现节录如下:
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找了一个小借口写了日记后——这首诗《深深地》写于2017年8月的第三个星期。在斯特拉特福(Stratford)的一条小街上,我用铅笔或滚珠(我必须检查一遍)写在一张纸上,也可能是旧信封、购物清单、笔记本页面,又或者是笔记本。这首诗歌的语言是二十世纪早期加拿大英语,当时的英语有短语“没那么糟”(less of a shit)。这个短语从来没在丁尼生的《悼念AHH》中出现过,但可能出现在乔叟的方言故事里。2017年12月,我从抽屉里拿出这首诗,勉强辨认出了笔迹,将它打成了一份电子文档。我是从文档的时间记录上,了解到了这些。
这首《深深地》,一首符合它的时代精神的诗歌,却声称自己不符合它。这不完全是死亡的象征,更像是生命的象征。
引用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的一句话,“光明,只存在于黑暗中,只存在于垂死的生命中。”(Only in dark the light.Only in dying life.)
诗歌,就像其他事物一样,是在特定的时间里创作的,诸如公元前2000年、公元800年、十四世纪、185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等。它们也存在于某个特定的地方,诸如美索不达米亚、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写它的人恰好在一个地方,在诸如书房里、草坪上、床上、战壕里、咖啡馆里、飞机上。诗歌通常由口而发,然后诉诸面上,这些面有像黏土、纸莎草纸、牛皮纸、纸、屏幕,同时它要借用某种书写工具,像铁笔、刷子、鹅毛笔、钢笔尖、铅笔、滚珠、计算机,还有特定的语言,像古埃及语、古英语、加泰罗尼亚语、中文、西班牙语、海达语。
一首诗歌总会承载某种信念,诸如赞美上帝、歌颂爱人、褒扬公爵夫人、挑战权力精英、思索自然或者生物、呼吁平民抵抗、呼唤全面跃进、谈论前任或者父权制,种种差异良多。一首诗歌如何编织,诸如高贵的语言、音乐伴奏、押韵的对句、自由诗、十四行诗、比喻、恰当的方言、俚语、脏话、大满贯时的夸口,也会受到潮流的影响。
诗歌的受众包括女神祭司、国王和宫廷、知识同侪的自我批评小组、民谣歌手搭档、时尚潮流搭档、垮掉派队友、创意写作101班、网路粉丝,正如艾米莉·狄金森所说,你的无名同伙(your fellow nobodies)。还有诗人一次又一次在所在之处掷出疯狂的话,他们被流放、被枪毙、被审查。在独裁统治下,愁眉苦脸的游吟诗人令人不安:在错误的地方说错误的话,会惹上一大堆麻烦。
每首诗都是如此:诗歌深深镶嵌在它们存在的时间和地方。它们不能抛弃自己的根。幸运的话,诗歌会超越它们的根。这意味着,后来的读者欣赏这些诗歌,尽管并不是以它最初的方式。美索不达米亚女神伊丝塔(Inanna)赞美诗非常吸引人,但它们不会像古代读者那样,阅读它就像骨髓融化到我的骨头里:我不认为伊丝塔会随时随地现身,伊丝塔会把几座山夷为平地,当然我可能是错的。
浪漫主义者一直在谈论永恒的名声和为时代写作,但写作没有所谓的永恒。名声和风格此起彼落,书籍也会被唾弃,被焚烧,后来或许又被发掘,被回收。今天的歌者很可能成为后来的歌者的燧火,就像后天的燧火会从火焰中取出,保存到颂歌和浮雕之中。塔罗牌中的命运之轮(Wheel of Fortune)实际上是一个轮子,这是有原因的。天有不测风云,至少有时候是这样。没有所谓的命运。根本就没有。
电影《邮差》(Il Postino)里的快递员偷了聂鲁达的诗歌,并算在自己的账上,以此来为自己的爱情歌唱。“诗歌不属于那些写诗的人,”他说,“它属于需要它的人。”事实上,当这首诗歌从写下它的人的手中流失掉,当这个人告别这里的时间和地方,这首诗歌就会像原子一样消散,还有谁真正拥有这首诗歌呢?
钟声为谁而鸣?亲爱的读者,为你。这首诗歌是为谁而作?也是你,这首诗歌为你而作。
阮清越谈后特朗普时代的文学
《特朗普时代的文学》
“疫苗有了。川普走了。2021,生活有点正常了。但一切将不同以往。”2021年新年开年,《纽约时报》策划“Let's Start Over(让我们重新开始)”,邀请十几位作家,谈论未来的政治、时尚、城市、文学、教育。“美国就像一张破损的挂毯,被一只宇宙之手拉扯着,越扯越硬。美国现代历史上最邪恶的分裂主义者、最肆无忌惮的自私自利的总统,最终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这场本应给予我们共同目标的流行病,使我们彼此对立。”弗兰克·布鲁尼(Frank Bruni)在谈政治的文章中写道。
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戳穿了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政策的虚无。在美国社会,自由主义者们都热衷于移情,但这并不妨碍自由主义者白人屏蔽和歧视黑人,后者在文化版图中只占有极少一部分。艾美·塞塞尔(Aimé Césaire)、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格洛丽亚·安扎尔杜亚(Gloria Anzaldúa)被视为激进主义者,而被排除在文化版图之外。
阮清越举了移民文化的例子。在特朗普时代,移民和难民被妖魔化。但大量的移民文学仍然视定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为美国梦,移民是崇高的,而结构性不平等问题是被漠视的。大多数移民作家和持多元文化主义的作家都没有解开这个面具。例如露易丝·格丽克。
阮清越提及了娜塔莉·迪亚兹(Natalie Diaz)的小说《后殖民主义爱情诗》(Postcolonial Love Poem),杰斯·罗(Jess Row)的散文集《白色飞行》(White Flights),克劳迪娅·朗金(Claudia Rankine)的诗集《只有我们》(Just Us),莱利·朗·士兵(Layli Long Soldier)的诗歌《鉴于》(Whereas),索尔马兹·谢里夫(Solmaz Sharif)的诗歌《看》(Look)。
最后,阮清越引用努尔·印地语(Noor Hindi)新近发表的一首诗歌,《去他妈的手工艺讲座,我的人民正在死去》(Fuck Your Lecture on Craft,My People Are Dying),其中写道,“殖民者书写鲜花,而我想做关心月亮的诗人。巴勒斯坦人在监狱里看不到月亮。”
阮清越是越战难民。后来回忆越战,他写道,“我的家人和其他难民逃到美国,带来了各自的故事,但除了自己人之间交流,多数不为外人所知。漂泊海外的越南人多达四百万,与多数相比,我的家人已是幸运。战争期间,三百万越南人失去了生命,我的亲人无一伤亡;成千上万越南人在乘船海上逃难过程中命沉海底,我的亲人安然无恙。”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阮清越直言自己不会期待美国会展现出良心,“请记住,不要指望这个体系的良心,他们不会认为战争是地狱,因为战争是他们的财源所在、兴隆之基。”
此前,在答钱佳楠的访谈中,阮清越提到《同情者》(The Sympathizer)的难民故事的特殊性,以及他本人对美国战争叙述的失望。“难民故事引入了其他一些元素,会打破这种移民叙事以及美国梦的神话。这些元素包括最根本意义上的,很多难民来到美国是因为美国对他们的家园做了些什么。……回头看美国文学对 越战题材的处理,这部分的经验在文学中是断裂的。多数是美国作家写战争,然后是越南裔作家写在美国的难民经历。也有难民涉及战争和移居两部分,但是他们写的是越南期间作为平民的经历和之后作为难民移居他乡。能够写战争故事的越南士兵用越南语写作,也就是说他们的书英语读者读不到。于是,美国人仍然主宰了对这场战争的话语权。”阮清越回答说。
《忠诚》(The Committed)
阮清越是普利策小说奖、麦克阿瑟天才奖、古根海姆奖的获奖者。阮清越现任教于南加州大学。新作《忠诚》(The Committed)将在今年推出。《忠诚》的内容涉及贩毒、左翼、难民、黑社会、法国。
让-菲利普·图森新作《情绪》
在欧洲局势笼罩在疫情、气候危机、民粹主义的阴霾下的今天,让-菲利普·图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出版了新作《情绪》(Les émotions),勾勒了政府和国际争端的大致样貌,和个人对当代历史的悲悯,探索了今日欧洲身份的模糊性、复杂性、焦虑。“自二战以来,欧洲经历了两个重大周期。首先是进步的周期,道德和人权领域取得了渐进的进步,这个周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截止。接着是自由主义的周期,它持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为止。今天的世界正在处在民粹主义的周期之内,人们对精英和代议制民主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图森总结道。
让-菲利普·图森
《情绪》一书很好地结合了两方面,亚历山大·拉克鲁瓦(Alexandre Lacroix)在《哲学》杂志(Philosophie)撰文评论说,其一是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具体想象,其二是精英主义的叙述。将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图森完成了这个任务。
正如书名所暗示的,《情绪》关注的是情绪,而非智力。主角或者叙述者是一位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让·德特雷兹(Jean Detrez)。一方面,德特雷兹深陷于技术体系和权力机器之中,他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具有掌控力;另一方面,德特雷兹的内心出现了空洞,自己的情绪变得越发不和谐,无法预测和难以理解。图森用细致而精确的书写,构造出缓慢而漫长的场景。相较之下,情节压缩到了极致:他发现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U盘,卷入了一个阴谋。
书中最重要的一个段落是,德特雷兹看着父亲的尸体,挣扎着做出情绪上的反应,可他却只能识别应有的情绪:“我察觉到情势里所隐藏的情绪,但却没有感受到这种情绪。或许我的精神过度紧张和机敏,它聆听到了我所感受到的,或者我应该感受到的。可是我无法真正感受到它们,我只能在外面观察它们。在这种微妙的区别中,我见证了我的性格:僵硬,病死,表达情感时会遇到种种困难。”
图森和让·艾什诺兹(Jean Echenoz)等人的作品被认为是“新新小说”(Nouveau Nouveau Roman),这一流派继承自新小说而来。像新小说一样,新新小说大多是午夜出版社(Minuit Press)扶持的。学者赵佳引述苏菲·贝尔托(Sophie Bertho)等研究者的说法指出,新新小说家们继承了新小说家们对文本机理的关注。新新小说家们尤其热衷于叙事,推动了“对小说性的真正的革新”,既“给予虚构以地位”,又“从内部予以破坏”。新新小说家们有“同一种发明世界的意志”,同时又发现参与创作计划的最好手段是“全身心地沉醉于笑的虚构中”。
图森和新小说家和新新小说家有些微不同。图森的独特之处是,黑暗而尴尬的超现实主义幽默,例如那些在图森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时刻,或者令人坐立不安的场景。在《逃跑》(Fuir)中,玫瑰色的雾霾一直笼罩着。在《玛丽的真相》(La vérité sur Marie)中,有人试图在东京机场将一匹纯种马送上货运飞机。在《裸》(Nue)中,一家巧克力工厂发生了毁灭性的火灾。在La clé USB中,叙述者试图在不做笔记的情况下发表一篇主题论文。正如图森自述,“在作品里,我是把事物放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而时间和空间本身就是非常细节化的。”
图森的极简主义、实验手法、超真实模拟在“玛丽系列”(MMMM)四部曲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难怪学者沃伦·莫特(Warren Motte)称之为“琐碎的史诗”(epics of the trivial)。四部曲包含《做爱》(Faire l'amour)、《逃跑》(Fuir)、《玛丽的真相》(La vérité sur Marie)、《裸女》(Nue),分别创作于2002年、2005年、2009年、2013年。故事发生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地点置于亚洲几个国家,故事仅是叙述者我和玛丽之间的爱欲和情感。四部曲的最后,我和玛丽再度相爱。“我们在黑暗中拥抱着对方,带着激情,带着悲伤,带着信任,带着爱,我感到怀里的玛丽是如此脆弱……玛丽有点惊讶地对我说、对我呢喃:‘那么,你是爱我的咯’”。
在一篇随笔性自述论文里,图森区分了两种概念,急迫和忍耐,它们是需要作者调和的一对关系。“急迫需要冲动、激情和速度,而忍耐要求缓慢、坚韧和努力。然而在写书的过程中,它们俩都是必不可少的,所占的比例有所变化,分量各不相同……卡夫卡,每天晚上,都坐在书桌前,等待激情推动他去写作。他对文学有这种信仰,而且只相信这一信仰(我不能也不愿成为其他任何人,他说),于是,他每天晚上都想着这一无法企望的美事降临到他身上:写。”
图森于1957年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父亲是比利时《晚报》(Le Soir)驻法记者,母亲是立陶宛裔书商,他的大部分时间在巴黎度过。图森于1979年、1980年分别获得巴黎政治大学和巴黎大学的学位。不同于其妹妹安妮-多米尼克·图森(Anne-Dominique Toussaint)选择进入影视行业,图森选择了文学。图森在写作生涯初期就认定了新小说,后来在午夜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作品,《浴室》(La Salle de bain)。八十年代起,图森也参与到电影制作中,先后参与了三部电影,《先生》(Monsieur)(1990年),La Sévillare(1992年),《溜冰场》(The Ice Rink)(1999年)。此外,图森还涉足摄影艺术。
作家阿米特·乔杜里
2020年12月1日,阿米特·乔杜里(Amit Chaudhuri)在母校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写小说?:它是否源于生活?是否真实发生过?》的在线演讲,《n+1》做了全文刊载。
整场演讲,乔杜里都在围绕“我为什么真的在写小说?”这个问题展开,或者如乔杜里所说,这是两个问题,“这是来自你的生活吗?这是真的吗?”乔杜里先是回应了人们对他的小说的质疑,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并非传记或者回忆录,尽管连媒体都称之为自传类小说——当然,乔杜里会反驳说,并不存在自传类小说。
让-菲利普·图森
乔杜里的第七部小说《少年时光的朋友》(Friend of My Youth)的确和他的生活存在某种相关性。说句题外话,小说和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的某部作品重名了。小说主人公或者叙述者就是阿米特·乔杜里(Amit Chaudhuri),这位朋友是拉姆(Ramu)。拉姆有毒瘾,后来进了康复中心,并从此从他的世界脱逃了。两位乔杜里都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他们都写了《少年时光的朋友》,在泰姬玛哈酒店(Taj Mahal hotel)交换了母亲和妻子送给他的两双鞋,在牛津大学读书,并尝试做音乐。
乔杜里对上述答案最直接的回应是:在《少年时光的朋友》中,生活中的那些故事没有发生。再进一步讲,情节无关于故事,情节不是一个现实,情节是一种虚构。根本上讲,引用乔杜里,“时间在无畏地前进”。
“困难在于对叙述氛围的抗阻,叙述氛围是某种东西已然结束的氛围……‘显示,而不是告知’,这是一个空洞的指令,更真实的关键是‘如何不去重述,如何叙述当下’,‘显示’和‘告知’会被镶嵌在其中。”乔杜里如是声称。乔杜里似乎错误地引用了《写作的零度》中的例子,该例子并不见诸于该书,但乔杜里恰当地延伸了他的回应:小说之为小说,正在于它已将“公爵夫人五点钟走了出去”变成一种基本的叙述,而非其他,它在其中经受了一种驯化。再次借用乔杜里的一个比喻,写作即作曲。
纳博科夫提出并反对的“潜意识坐标”(subliminal coordinates),也正是乔杜里所反对的。或许乔杜里的反对更为彻底。1999年和2000年,乔杜里意识到英国文学和印度英语文学现场的同质性(homogeneity),它涉及国家境况、多元文化、戏剧独白、乌托邦经验等等因素,就连石黑一雄、伊恩·麦克尤恩、布克奖也不例外。
后来,乔杜里拿出了他的行动,他发起了文学行动主义(literary activism)。2014年,乔杜里发起了研讨会,并发表了《使命宣言:论文学行动主义》(Mission Statement:On Literary Activism)。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如乔杜里所言,出版系统接管了文学系统,原有的评价标准被废弃,新的标准将以文化资本的方式制定,乔杜里将之命名为“市场行动主义”(market activism)。那些知名的作家也参与到“市场行动主义”之中,萨尔曼·拉什迪从之前的代理人那里叛逃,将自己的小说《撒旦诗篇》转交给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被哈珀·科林斯印度(Harper Collins India)主编潘卡·米什拉(Pankaj Mishra)发现了。相比之下,总部位于加尔各答的独立出版社海鸥(Seagull)受到了乔杜里的赞扬,海鸥获取了包括托马斯·伯恩哈德、恩古齐·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等在内的世界文学名家的版权。
乔杜里为文学行动主义,举了两个例子。其中一个是居住在英国的南非小说家佐伊·维科姆(Zo? Wicomb),她的声誉在德里克·阿特兹(Derek Attridge)的推动下得到了提升。另外一个是阿尔温德·克里希纳·梅赫罗特拉(Arvind Krishna Mehrotra)被乔杜里提名为牛津大学诗歌教授,但2009年评选在一系列的丑闻后不欢而散,直到2010年重新开始新的议程。
乔杜里,出生在加尔各答,像百年前的泰戈尔一样,家境优渥,叛逆而爱文学。乔杜里的母亲在少年时期会为乔杜里演奏泰戈尔的歌曲。从十九世纪开始,诗歌有两个伟大的谱系,其一是形而上学的,充满光芒和价值的;其一是论辩式的,但任意而武断,在《意外的泰戈尔》(The Accidental Tagore)一文中,乔杜里称他曾以为泰戈尔属于前者,但他越来越相信泰戈尔属于后者。乔杜里的加尔各答还有,纳萨尔派运动(Naxalite movement)、杜尔迦女神(Durga)。
在写作小说、诗歌、政论文章之外,乔杜里还做音乐,主要有印度古典音乐和实验音乐。乔杜里发行有两张专辑,This Is Not Fusion和Found Music,今年他自主发行了Khayal In Gujri Todi and Madhuvanti,2002。他的女儿,阿鲁娜(Aruna)是一位流行音乐人。他的妻子是罗辛卡·乔杜里(Rosinka Chaudhuri),牛津大学首任全球南方梅隆教授(Mellon Professor of the Global South)。目前,乔杜里任教于东英吉利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主持创意写作课程。
中东欧知识分子奥克萨纳·扎布日科
2021年1月1日,今年第一期《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刊登了对乌克兰作家奥克萨纳·扎布日科(Oksana Zabuzhko),扎布日科是欧洲最具有探索精神的知识分子之一。此前,Amazon Crossing出版了由哈利娜·哈林(Halyna Hryn)、阿斯科尔德·梅尔尼乌克(Askold melnyuk)、尼娜·穆雷(Nina Murray)、马尔科·卡林尼克(Marko Carynnyk)、玛尔塔·霍班(Marta Horban)所翻译的故事集《你的广告可以放在这里》(Your Ad Could Go Here)。
奥克萨纳·扎布日科
书中第一个故事是《哦妹妹,我的妹妹》(Oh Sister,My Sister),故事讲述了主人公见证母亲,一个政治迫害者,放弃了第二个孩子。“她用她冰冷躯体的全部力气,对那一小块生命说话,她绝望地钻进了她的内心深处,请原谅我。原谅我,宝贝,我亲爱的女儿或儿子,我亲爱的——你的母亲因为恐惧而不敢吮吸你。”故事反映了扎布日科在其他作品中的诉求,集体历史对个人命运的摧毁性影响。
在扎布日科的故事里,她向留驻了诸多压抑和暴力的女性身体和女性命运投注了很多注意力。在这些故事里,过去的创伤不断重新:校园女同性恋,被强奸的歌手,置身在男性欲望下的女孩。“在公园的长椅上,女孩们疯狂地缠绕在一起……当艾菲亲吻达卡眼睛下的泪痕,把她的嘴唇贴在她的嘴唇上,愕然喘息着,刹那间,艾菲的心跳在达卡的胸膛里,两个人都僵住了……”《女孩们》(Girls)如是写道。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克莱坦涅斯特拉、奥菲利娅、格特鲁德、灰姑娘。
扎布日科的主题还有国家认同。《古斯塔夫的专辑》(An Album for Gustav)讲述了一个外国摄影师和参与橙色革命的年轻夫妇的邂逅。摄影师向读者宣告,西方社会无法理解和想象乌克兰;而年轻夫妇则象征着乌克兰的未来,象征着乌克兰丰富而美好的未来。
与此同时,乌克兰在历史之中是消声的,是沉默的,扎布日科这一代继承了历史的沉默。在扎布日科看来,中东欧的作家群体开始为沉默的历史和死亡发声,而今时今日的这个群体,可以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拉美文学相提并论。
扎布日科于1960年9月19日生于卢茨克(Lutsk),其父亲斯蒂芬·伊万诺维奇·扎布日科(Stefan Ivanovich Zabuzhko)是一位作家。从1968年开始,扎布日科就生活在基辅。扎布日科在基辅大学学习哲学,并于1987年获得美学博士,随后在各大院校任教。目前,扎布日科在乌克兰国家科学院一个哲学研究所工作。1994年,扎布日科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
扎布日科被认为是后切尔诺贝利一代。切尔诺贝利象征着核威胁和世界末日,也象征着苏联意识形态的终结。《乌克兰性的田野工作》(Field Work in Ukrainian Sex)、《被遗弃的秘密博物馆》(The Museum of abanded Secrets)是扎布日科最知名的虚构作品。《乌克兰圣母院:神话冲突中的乌克兰女人》(Notre Dame d'Ukraine:A Ukrainian Woman in the Conflict of Mythologies)是扎布日科最知名的非虚构作品。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张艳
电脑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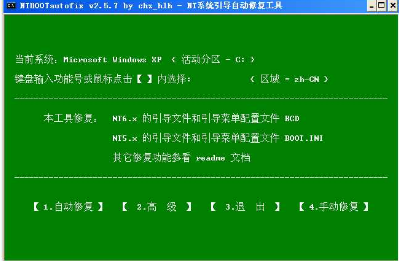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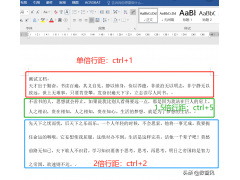

![RedHat服务器上[Errno 5] OSError: [Errno 2]的解决方法](https://img.pc-daily.com/uploads/allimg/4752/11135115c-0-lp.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