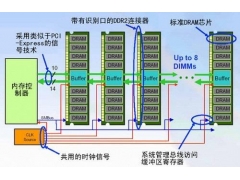西西是香港文学重要作家,原名张彦,广东中山人,1937年生于上海,1950年随父母移居香港,曾任教职。西西的著作多元,包括诗、散文、长短篇小说、书评等四十多种。代表作有《我城》《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候鸟》《飞毡》《哀悼乳房》等。2022年5月23日,西西获第十六届香港艺术发展奖之“终身成就奖”。
下文刊发新京报书评周刊的特约记者于2018年对西西的报道,作为纪念。
提起香港作家,不少读者都会想到西西——或者至少,这一定是蹦出脑海的前几个名字之一。
这么多年来,从《我城》到《飞毡》,从《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到《哀悼乳房》,西西的写作似乎跨度很大——有短篇有长篇,亦有杂文散篇。
西西,香港作电脑家,1937年生于上海,1950年随父母定居香港。曾任小学教师,后专职写作。代表作《我城》《哀悼乳房》《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毛毡》等。
如果要为这些创作捋出一个脉络,还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所以,倒不如听西西自己来说。在西西看来,这些文字与写作,也不过是去做令她高兴、自然的事情的结果。卡夫卡说写作是“拆掉生命的房子建造小说”,那么关于一个作家最深的秘密,可能也就都藏在她的小说里。
撰文 | 一把青
上周去清迈,在周六市集的摊位上买到几本《南国电影》,半世纪前香港邵氏电影旗下的宣传杂志,故纸堆中的旧星光,当地人与旅游者多不识,相遇于异乡的夜色中,老灵魂如我者却狂喜,速速揽下,随手翻开,一篇《重访凌波》,谁写的?西西。
“那天,我跑进影城去玩。你知道,我常常跑去影城去玩的”,开篇这样写,像个跑来跑去玩捉迷藏的女孩,熟悉吗?唱着《访英台》掀起黄梅调旋风的梁兄哥凌波,早退隐幕前不问江湖事,而此西西正是彼西西,文坛屹立五十年,早前更击败余秀华、北岛、西川等后辈,获得第六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香港作家,提名词形容她,“香港文学过去经常被视为次等,西西或谐或庄的诗歌道出了这个城市及其居民的品格,她的诗歌也证明了一个城市的故事不必是宏大的叙述,而可以是表面琐碎的絮语、寓言或者童话“,官方的表达尽管精确,却显得沉重了几分。
一
我认知中的西西是什么样的呢?举两个例子,一是某年香港书展,陈列不少作家小物,像张爱玲的手稿、林燕妮的坤包,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兴奋地扑到橱窗前,对着几个玩偶惊叹,“这些是西西《缝熊志》中的熊仔呀”,2009年,因癌症化疗后遗症右手失去知觉,需做物理治疗的西西,把自己多年来为训练双手缝制的毛熊玩偶集结成书,看似手工集锦,而衣饰模样皆有历史考究,皇帝熊、曹雪芹熊、水浒传熊、凯撒大帝熊,包罗万有似是人类学博物馆,西西1937年生于上海,1950年赴港生活,出书时已70岁,但并未居庙堂之高,还能让年轻人,亲近得仿佛故友重逢,就像是这个笔名的起源,“西”字即一个跳房子小人迈开腿的形象,叠字“西西”就是从一个格子跳到另一个格子,平淡清浅,又饱含情义。
另一件事,是听闻香港中文教材常年收录西西的文章,遂向一位香港同事提起,寡言的中年男子,听到我的问题却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当然啦,不读西西读什么?”的确,西西的文字,她的城市随想与自我探寻,已与这片土地紧紧交织,滋养几代人,又润物细无声。
《我城》,作者:西西 ,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
不读西西读什么?其中最典型的,要数《我城》,小说的创作背景,是70年代中期,西西认为文学上冷漠阴暗的调子不合她的个性,于是决定写个活泼的小说,关于年轻的一代,写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城,用他们的感觉去感觉,用他们的语言去说话。
于是有了中学毕业生阿果的故事,原型是她自己的弟弟,在电话公司工作,把每天的故事告诉西西,她在厨房里完成了小说:阿果在父亲死后,一家人搬往新居,引出一连串的人物,小学生、公园管理员、木匠、家庭主妇、航海电工,以及一系列社会事件,石油危机、环境污染、香港水荒、治安问题,植根于生活的故事,西西又施以童话化的魔法,尖沙咀是肥沙嘴、狮子山隧道变成睡狮山隧道,麻将消遣,是四个人围着打“透明软糖”,小说第一句“我对他们点我的头”,奇特的文字,把人吸引入桃花源,像徐徐展开的画卷,直到结尾那句“再见白日再见,再见草地再见”,城市身世的来龙去脉蕴藏其中,再拆解成一个个微小的我,灵动鲜活、充满盼望,众志成城,同舟共济。
我们读到《我城》,隔着时差回望,香港原来不只是繁华金粉地,马照跑舞照跳,也有过如此温情质朴的过去,她自白,“城市是有生命的,岂能不变,岂能当一块铁板去写”,马世芳也说,“西西写战争、死亡、贫穷,也带着一副柔软的心肠,和一双洞烛人世、然而始终好奇的眼”,经她的视角窥探,就像是《羊皮筏子》里,写女孩坐着小舟回望书籍发展史,从敦煌出土的白杨木汉简,到公元前2世纪羊皮纸的出现,“打开电脑一本书,坐在小矮凳上静静航行”,我们读西西,似乘桴浮于海,也能收获这样的雄伟波澜,和千帆过尽的宁静。
二
城市在变,人也在变,西西自己也是一样,我们乐于见到,每个阶段的她,都交出了漂亮的答卷。
前文提及的《南国电影》,邵氏电影麾下一众早期娱乐记者,西西、亦舒,皆是成员之一,而其后的走向,却大相径庭。亦舒深耕都市言情,启蒙现代女性周旋于爱恨,西西笔下的爱情,则以更中性化的角度看待女性问题,聚焦的不是情场如战场,而是更幽微寂寥的女人心事。
《像我这样一个女子》,作者:西西 ,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5月。
例如《像我这样一个女子》,主角是一位继承姑母手艺殡仪馆化妆师,她逃避自己的职业,怯懦于与男友的关系,开篇即阐明,“像我这样一个女子,其实是不适宜与任何人谈恋爱”,男友误会她仅仅是化妆师,她不解释也不说明,带他去自己的工作场所,真相大白,又将恋爱失败的悲剧性归咎给命运,她在面对男友时的种种想法,害怕失去,顾虑重重,其实是自我矛盾的镜像而已;再像《感冒》,32岁的小鱼到了年纪,听从父母之言顺理成章地进入一段婚姻,作者引用大量诗词映照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变迁,借一场长久的感冒比喻对婚姻爱情的种种不适,表现女性对现实的挣扎取舍,直至自觉应离开丈夫,感冒才稍有痊愈的迹象,她引痖弦的诗,象征自主性的回归,“可曾瞧见阵雨打湿了树叶与草儿,要作草与叶,或是作阵雨,随你的意。”
电脑《哀悼乳房》,作者:西西 ,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
西西对于自己的感情世界着墨不多,她单身未婚,与母亲妹妹同住,她笔下的爱情,冷静而有距离,又细腻得不可能与她无关,卡夫卡说写作,是“拆掉生命的房子建筑小说”,生活中的动荡与伤痛,西西都能熔铸进作品里,譬如经历乳癌,她写下《哀悼乳房》,治疗前后的彷徨、病中的疗程与食谱,她兼容并包,逐一收录,当然是小说家的职责所在,对病人即作者来说,却并非不是一件残忍的事;在更后期的《白发阿娥及其他》中,她又借老婆婆阿娥写自己的晚年心境,从小时候由大陆逃难来港,到教会领牛奶,到与越南船民擦身,回归前的移民潮,《照相馆》一篇,阿娥在结业前照相馆里独对旧照,当记忆和现实都面临消逝,结束处由幽森的黑房接入敲门的女孩和阿娥的应对,悬空了叩问。
在那些手法的尝试、魔幻主义与存在主义的使用之余,西西更崇高的意义,是她以自身印证了萨义德所言艺术家的晚期风格,是处理自身与时间抵牾的一种态度,终结了与秩序的纠结与交流,站在社会的边界,并将生老病死,凝练成小说的维度。
三
字里行间再百转千回,面对读者与大众时的西西,却仍是爽朗诙谐的。
前两年,台湾纪录片《他们都在岛屿写作》拍摄西西特辑,文友遗憾她患癌后右手难以持笔,影响写作进度,她却丝毫不以己悲,向镜头展示左手写字、在小小的家中如何借助筷子一只手拧干毛巾,兴致勃勃地带访者参观她念书和教书的学校,家旁边的市场与街坊,调侃自己过的清苦知足,笑言写作是一个人的事,“其实不只是家里人不理你写作,在整个香港也没有人理你写电脑作”。
《他们都在岛屿写作》西西特辑剧照。
话虽如此,但西西也说,“今天天气很好,待会儿,你去做你高兴做的事,我去做我高兴做的事。”
显然,写作就是西西高兴做的事,昂扬纯真,乐此不疲,一生最爱是天然。
文/一把青
编辑/走走、李永博
导语校对
电脑 电脑